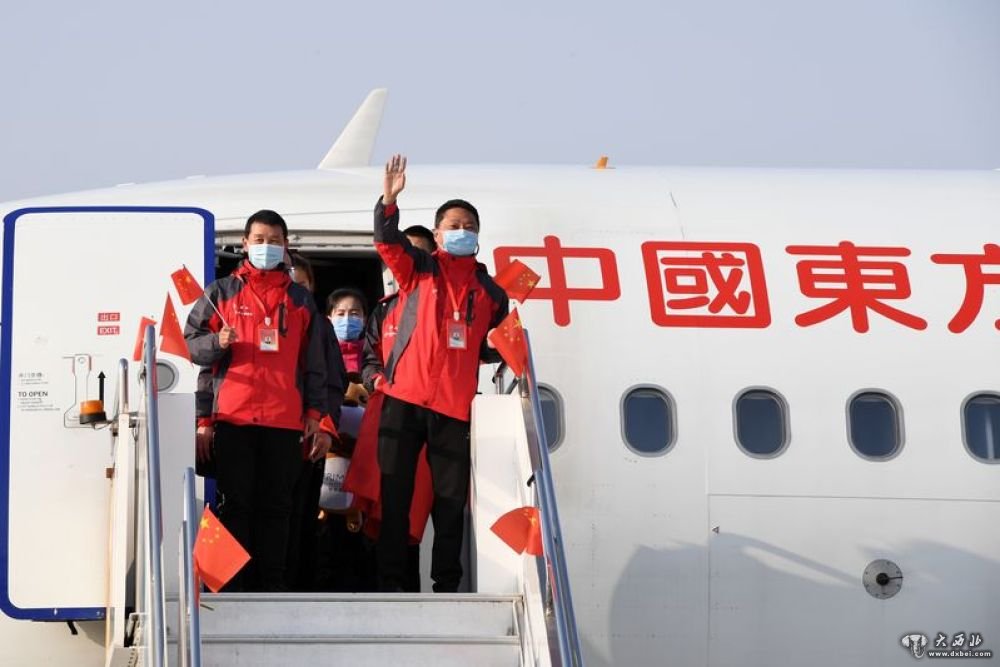她是世界电影史的传奇。说到世界电影史,提及纪录片,就无法回避里芬斯塔尔。
莱妮·里芬斯塔尔,生于1902年,死于2003年,可谓长命百岁。她去世当年,在中国艺术界和思想界都引起过热烈讨论,不仅因为她是位曾祖母级的世界著名电影导演,更因为她最杰出的影片乃为纳粹主义极权统治而拍摄。
里芬斯塔尔为世界电影史贡献了两部非凡的、史诗般的电影巨制:《意志的凯旋》和《奥林匹亚》。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1975年出版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篇评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对里芬斯塔尔进行了严厉抨击。此文几乎成为批判“法西斯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桑塔格也不得不承认里芬斯塔尔的电影“甚至是迄今最伟大的纪录片”。但里芬斯塔尔既不在乎桑塔格的“批判”,对“赞誉”也毫不领情,她压根就没把规则放在眼里。
里芬斯塔尔出生在德国一个小工厂主家庭,父亲严厉、吝啬、霸道,她却生性叛逆,而且极具艺术家天赋。里芬斯塔尔自小酷爱舞蹈,却在崭露头角时摔伤了腿改行成为电影演员;接着又因超凡脱俗的容颜陷入三角恋漩涡;随后,她一脚踢飞两位情人,走上导演之路,自己执导了电影《蓝光》。从这部电影开始,里芬斯塔尔便与法西斯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影的部分镜头需要在意大利境内拍摄,剧组进入意大利时因携带了两万多米的胶片和电影器材,需要缴纳关税。《蓝光》剧组的财务状况并不宽裕,里芬斯塔尔急中生智,立即给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拍去一份呼救电报。6小时后,剧组被免去关税顺利入关。时值1931年,她29岁。
1932年3月24日,《蓝光》在柏林首映大获成功,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奖。
此时德国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末期,被老朽而昏聩的兴登堡总统治理得一片狼藉,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却是德国新兴力量,德国人到处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希特勒。这种气氛也感染了里芬斯塔尔。
《蓝光》首映前的一个月,里芬斯塔尔在柏林体育馆聆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这使她天旋地转:“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随后,她从邮局给希特勒发出一封信:“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前不久在我一生中首次参加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听了您在柏林体育场作的一次演讲,我不得不承认,您和场上听众们表现的狂热之情深深打动了我,我很想亲自同您认识一下……”此时的里芬斯塔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注意到了她,不仅看过《蓝光》,甚至看过她主演的所有影片。希特勒立刻召见了她。
希特勒对德国人来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我对影片中的希特勒形象进行过反复观察,他的这种“魅力”在我看来极为古怪,那种充满神经质的举动不仅征服了里芬斯塔尔,也征服了整个德国。一个有力证据便是: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嫁给戈培尔,乃是因为她爱上了希特勒,嫁给戈培尔就可以经常看见她的偶像了。
这是一次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会面。希特勒面对里芬斯塔尔时显得平易近人,并迅即“爱上了”她,见面伊始就想拥抱她。里芬斯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发现我不是很情愿的时候,他马上就松了手,侧着身子对着我,举起了双手,向我发誓说:‘在我完成我的事业之前,我是不允许爱上女性的。’”
从此,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之间开始了“暧昧交往”,尽管她拒不承认自己爱上了希特勒,但希特勒却以“红颜知己”待之。里芬斯塔尔成为希特勒的座上客。
深陷法西斯主义泥淖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标志着纳粹主义走上了国家化道路。希特勒上台不久便邀请里芬斯塔尔前往帝国总理府,希望她加入政府:“我想交给您一个光荣的任务,依据您的才能也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您知道,戈培尔先生现在是宣传部长……您可以协助他担任电影和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但里芬斯塔尔对此表示了拒绝。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8月,希特勒再次将她请到总理府——里芬斯塔尔从此深深栽进法西斯主义的泥淖。
纳粹党将于9月份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邀请里芬斯塔尔正是为了拍摄党代会纪录片。这次会议被取名为“信仰的胜利”,于是,电影的名称也叫《信仰的胜利》。片子长达1小时,于同年12月1日公映。这是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党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虽然里芬斯塔尔对片子并不很满意,该片却在纳粹党人中大受欢迎。
1934年8月,里芬斯塔尔再度接到纳粹党邀请她拍摄本年度党代会纪录片的信件,尽管里芬斯塔尔声称自己一再推脱,但希特勒却认为只有她有能力拍好这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希特勒为了这部片子可是花了大价钱,无限制的经费使里芬斯塔尔组织了一个拥有36名摄影师、达170人的庞大摄制组。6天的党代会期间,里芬斯塔尔手下的摄影师穿着清一色的纳粹冲锋队制服,总共拍摄了13万米的胶片,经过5个月的剪辑,为世人留下一部有人激赏有人诟病、时长近两小时、史诗般壮丽的宏伟巨制——《意志的凯旋》,该片片头即标明“受元首委托制作”。1935年首映式结束,希特勒当即送给里芬斯塔尔一串精美钻石项链。这部巨制不久即为里芬斯塔尔带来巨大声誉,她一步跨入了世界顶级导演行列。
由于德国国防军对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凯旋》一片中给的镜头太少表示不满,里芬斯塔尔又于1935年度纳粹党代会期间,专门为国防军补拍了一部时长约20分钟的短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这是她为纳粹拍摄的第三部影片。
我们知道,德国是哲学大师辈出的国度: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即便在纳粹统治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信仰、意志、自由,是关涉人类精神最核心的超级词语,这些划时代的哲学家们终其一生,且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也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最终归宿。里芬斯塔尔却用电影宣告了人类精神的终结:信仰,胜利了;意志,凯旋了;自由的日子也如期而至。可就在她为希特勒拍摄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上映不久,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这当然不是说里芬斯塔尔制造了怎样的罪愆,但她在精神上与希特勒不仅暗通款曲,简直是心心相印:一个是在用“美”阐释极权,一个是极权主义的直接化身。
《奥林匹亚》拍摄于1936年德国柏林举办第11届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鉴于里芬斯塔尔的巨大影响,向她发出了邀请。里芬斯塔尔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极不情愿,但稀奇的是,她总能在“身不由己”的情绪下拍摄出惊人之作,《奥林匹亚》也是如此。奥运会是世界性的,但这一届却是德国的,希特勒要通过这次奥运会表达他的纳粹思想: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剪辑,影片终于完成,总长度约为3个半小时,分上下两集,上集叫《群众的节日》,下集叫《美的节日》。里芬斯塔尔亲自向希特勒提议在1938年4月20日上映,希特勒假作犹豫,随即答应了她的提议——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的生日。《奥林匹亚》再度引起轰动,公映不久便在欧美各国巡回放映。
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二战中,她希望自己能在战争中“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仁不让地组建了“一个电影工作组来为前线做战争报道”。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里芬斯塔尔给希特勒发去了贺电。直到二战后期,她还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
自由拯救莱妮
从里芬斯塔尔的履历不难看出,她与希特勒可谓“过从甚密”,也正是与希特勒的交往把她推到了事业的顶峰。二战结束后,里芬斯塔尔将面临什么,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盟军对她进行了4年的审查,仅冠以“纳粹同情者”予以开释。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像她这样的经历,枪毙十次也绰绰有余。
使里芬斯塔尔逃过劫难的正是西方文化中浸淫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位叫巴山姆的作家在采访里芬斯塔尔后不无奉承地写到:“里芬斯塔尔深信,艺术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独立于物质世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获得了创作艺术的自由,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确实,里芬斯塔尔是自由的:她拒绝了希特勒的情感邀约,回绝了希特勒的入阁邀请,对戈培尔的示爱公然表示厌烦。而她更大的“自由”来自于影片拍摄过程,不仅没有类似“主题先行”、“政治正确”的要求,更没有细节上的框束,即便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从没有在她的创作过程中给过任何“指导”——何况里芬斯塔尔根本不会接受这些。她给我们呈现的永远是一脸的坚忍不拔、不屑一顾。
正是“自由”地创作,才激发了她的天才想象,使她创造出充满极权主义色彩的华美篇章。里芬斯塔尔表示自己“向来关注美”,为了“美”,她可谓不顾一切,她自诩每一个镜头都源于“真实”,其诠释方式则相当标新立异。在《意志的凯旋》中,她把纪录片陈述性的语言改为叙事性的,创造性地把平面视觉立体化、复合化,使观众沉浸在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此时的纪录片所“纪录”的不再是“纯粹客观”,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铭刻着她表达自我的欲望。如《意志的凯旋》,开场便是希特勒的专机穿越厚重云层,绕过纽伦堡大教堂的顶端如神灵般降临地面;其大阅兵场面更使后来的所有大阅兵影片相形见绌。影片使人们相信,只有希特勒才能拯救德国,希特勒就是德国的上帝。里芬斯塔尔在不知不觉中把希特勒神圣化,并且通过这种“神圣感”鼓动起了纳粹意识。
里芬斯塔尔把纳粹精神与“美”结合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使观众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她对纳粹主义的宣传,当时,有相当多的德国观众就是在看了里芬斯塔尔的影片之后臣服于纳粹的。如果说希特勒用谎言欺骗了世界,那么,里芬斯塔尔则用“美”欺骗了世界。尽管如此,里芬斯塔尔却从不承认她所拍摄的是宣传片,坚决否认自己是纳粹宣传家。她确实没与纳粹建立过任何官方联系,而始终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在进行工作。
温家宝总理曾引萧伯纳名言“自由意味着责任”,此言极好。作为艺术家,如果不能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就不能够自由地表达。一旦艺术家失去创作自由,不论其作品呈现怎样的大义,都不会是来自艺术家的心灵,而只能是虚构。然而“自由”的另一面,是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当里芬斯塔尔以独立艺术家身份行使自己职责时,她应该问一问自己:“自由”到底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不论是谁,只要身处极权社会,就没有自由可言;只要有一个人身陷极权之囹圄,那么所有人都不会自由。今天对里芬斯塔尔拷问,并非因为她为希特勒拍摄了4部电影,而是她拒绝忏悔。(正如某大师对自己的“文革”经历选择性失忆一样,里芬斯塔尔不承认自己“有罪”,大师却是假装“记不得”。仅此,就注定他永远无法达到里芬斯塔尔的高度。)她总是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桑塔格讽刺道:“在真相和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而里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里芬斯塔尔有愧于自由,也有愧于“美”。
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里芬斯塔尔作为“独立艺术家”身份的工作,而是来自盟军对她的审判,这个审判真实地秉承了自由主义所恪守的价值——意图和行为是罪与非罪的界限。精神的无罪即自由宽恕了她。拯救里芬斯塔尔的正是与法西斯主义完全对立的自由主义情怀。此后,她继续保持着自己对“美”的激情,在别处释放得同样耀眼。
虽然里芬斯塔尔取得了艺术上的至尊地位,这一成就却成为悲剧性范例。它提醒我们,不论如何“独立的”艺术家都应懂得:自由,不应是屈从于极权的工具;“美”,也不该是取悦于极权的资本。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会有纯粹的艺术,也不会有纯粹的“美”,只有彻底扼制极权主义的膨胀,艺术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艺术也才拥有真正的生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