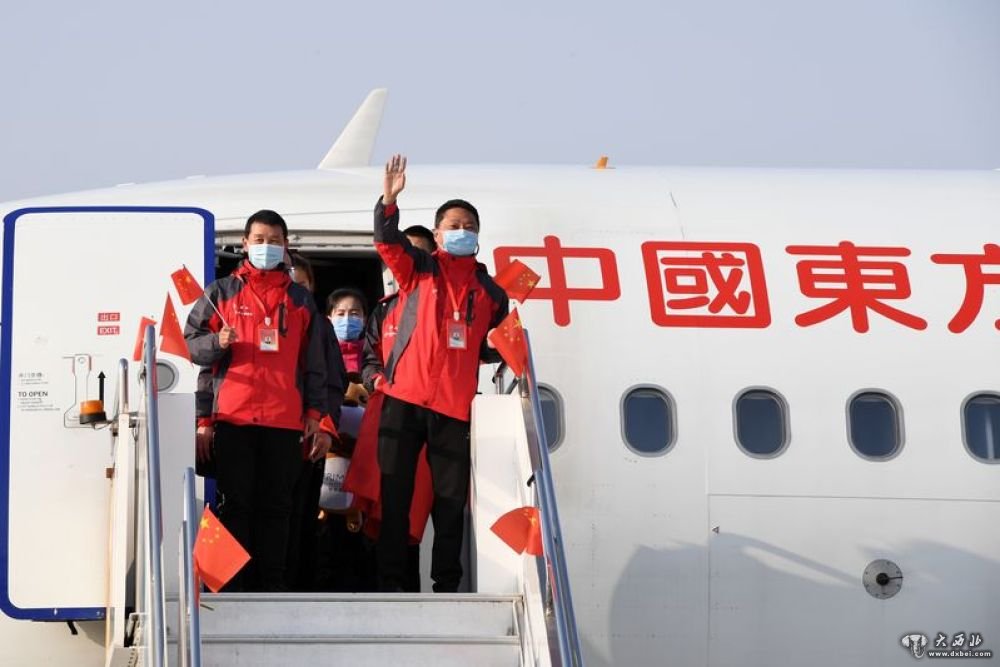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撤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天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旬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原刊1944年9月《小天地》月刊第1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