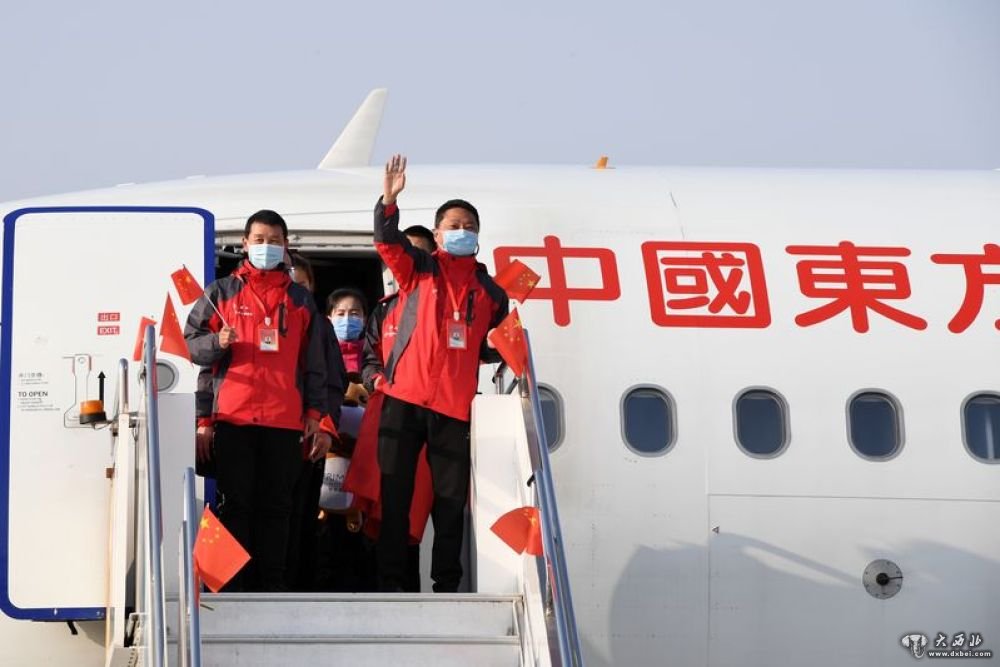有什么是千年不变,万古如斯的?
散步时无所事事,稍一驻足,听到耳边的风声,很熟悉,这不就是1958年春被贬下乡时,一路听到的单调而又时高时低的风声么?原来风声也是天籁,该来时它就来了,该高亢它就高亢,该低吼它就低吼……它是东西南北来来往往的气流形成的,不为人事所左右。你不注意它,它就“如春风之过马耳”,你一留神或一不留神,它就突然从你耳边擦过。风声是永远不变的。
“边秋一雁声”,大雁的长唳也该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永远,说的是物种进化有了大雁这一族类,直到有一天大雁物种也像许多所谓珍稀动物一样灭绝。但今天在我居住的北京,秋天已经很少见到大雁,听到雁声了。
什么不会灭绝?我说:石头。一是它数量大,一是它坚硬顽固,还有大家忽略了的,它还会不断地产生,当然极慢,如喀斯特地貌中、岩洞中滴滴钟乳,以一百年一公分的速度(似乎叫迟度更合适)凝结为钟乳石。不算慢啊。你想想地球冰河期那顺流而下的大石块又是多少万年形成的?难得的是从那时候起保留至今———我在山西五台山中台顶上看到的,在从青海跨阿尔金山去敦煌路边看到的,那一块块好像陨石一样的形状各异的巨石,想来就都是当年(这个当年可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乃至几十年前的事情)由汹涌的冰川裹挟夹带而来的,你就知道那“上善若水”的冰川有多大的冲击力,才能“以柔克刚”,当时如有人在,面对这冰啊水啊,意识中绝不会泛起这个“柔”字来。
当然,随着人类物用日繁,也会渐渐动起石头的脑筋。首先就是用石头挡水,多半是原形原状,筑成堤坝,充填围堰。盖房子,石室或石墙,取材于石,或会打打凿凿。最可恨的是开山修路,把山间岩壁炸个血肉横飞,然后,有些大块的没用就弃置一旁,等着水泥厂拉走碎尸万段,化作齑粉。侥幸留下来铺路垫底的,也都先弄成了小石子,不复原来的风骨,也就是彻底“改造”了。谁还知道它们前身就是亿万斯年经由“水成”、“火成”而成为石头的历史呢?
偏远边鄙之地的石头有福了。但人类总是喊着开发开发,对有生命的动植物斩尽杀绝一逞霸权之后,谁知道哪一天又要到遥远穷荒之地,动那里无主的石头?
李商隐写隋堤“终古垂杨有暮鸦”,错了,过于乐观了。本来,有树林处有暮鸦,何限于垂杨?这才一千多年下来,不但隋堤,所有的城乡、园林,大道小路边,即使还有些落叶树,树上还剩多少鸟巢?晨昏还有多少鸟出林归林?京杭大运河的堤岸上还有多少棵垂杨?风景已殊,正如山河之异。这是前之古人所逆料不到的。
谁还能轻言“终古”?不但不敢预言万载,千年也不行。天地间好风景正在人类的践踏下毁坏,消失,每一天,每一刻。
也许,只有其生命堪称永恒的日月,悬诸高天,经行不息,笑红尘中妄人自比金乌,转瞬而逝。人类也有对日月特别是对太阳的超乎什么黑点爆炸以上的灾难的预言,且不管它。而我们所见的日色月色,尤其是在城市包括中小城镇所见,已与在藏北高原和青海湖边所见大大不同。而据说我们要到2015年,北京的pm2.5才可望略有改进。
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暂写至此,还可以接着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