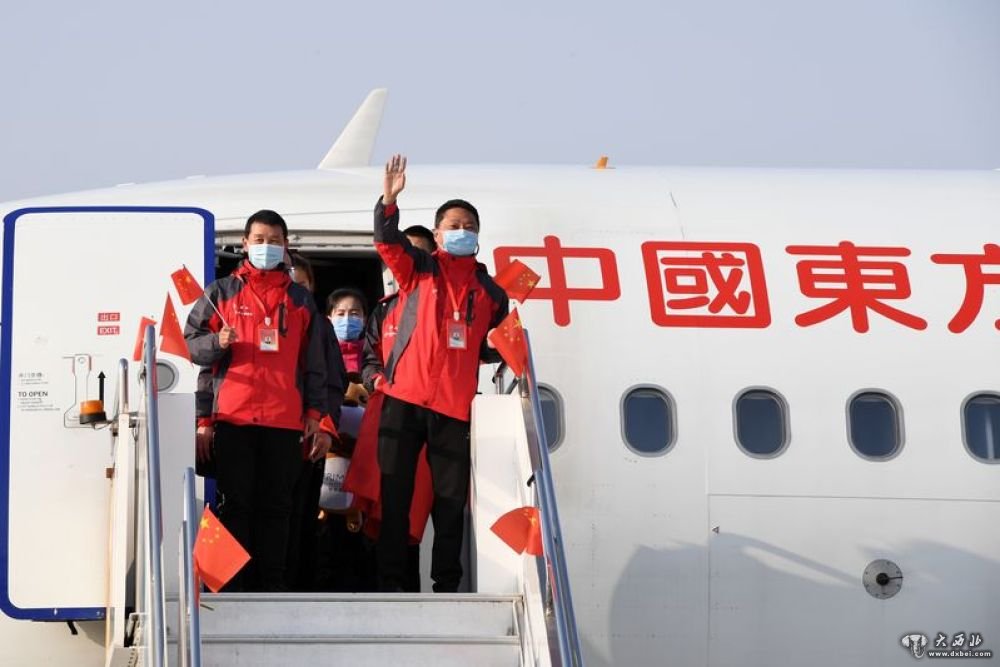但检察长季楠没有制止溥仪的陈述,法官们也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由,驳回了辩护方的意见。
溥仪继续陈述,“所谓的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纮一宇'.’八纮一宇‘这四个字源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两种--剑和镜给我了。”
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崇拜神道。根据法律,不敬神社者要处以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
根据统计,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的五年间,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各处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从此走过,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
按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占领东北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伪满洲国”划归日本,将东北地区“改祖换宗”,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成“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一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
“八纮一宇”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皇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
黄绢信
溥仪第二次出庭后,直讯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
然而,这只是直讯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
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日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
日本律师鹈泽聪明首先上了场,兜着圈子让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
很快,一个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
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为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璈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
布莱克尼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日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
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刁蛮可见一斑,而他的执业能力更不容小觑。
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
8月20日,布莱克尼与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鹈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地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作答。
21日,布莱克尼的提问仍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卫勃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
布莱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
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
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
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
布莱克尼问:“上面的御玺也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
局面发生了反转,布莱克尼迅速反扑:“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提出建议:鉴定此信,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当时的新闻媒体纷纷大篇幅对“黄绢信”一事予以报道,文章重点大多放在了“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上,讥讽布莱克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走下证人席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
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