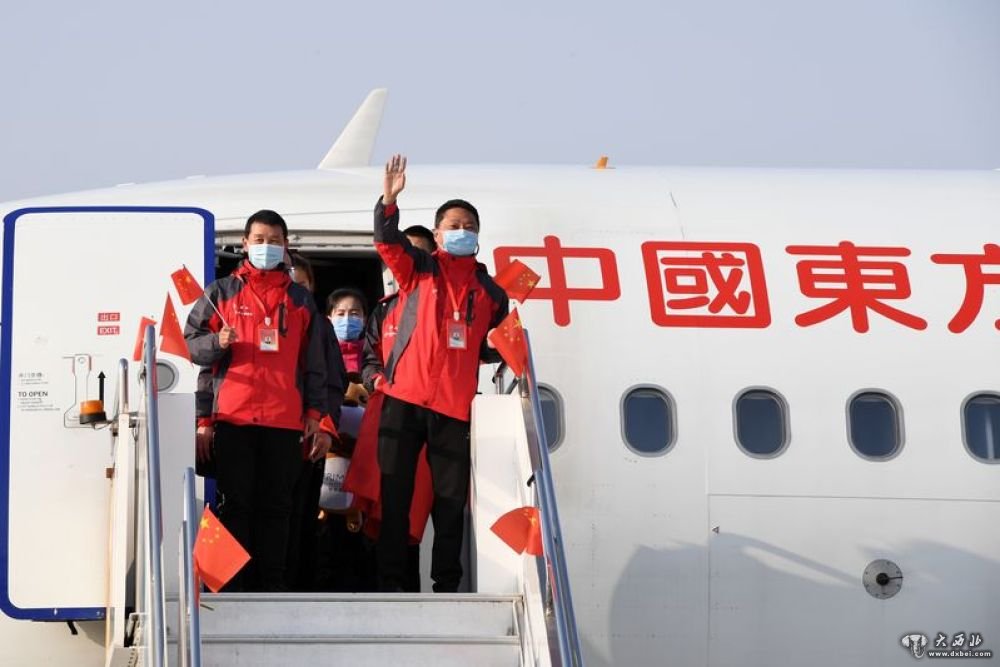登锁是个有力气的人。他的手掌大,胳膊壮,全身长满了肉疙瘩。携着这些肉疙瘩,他来到温州城时不气短。他先进了打火机厂,坐在车间里装搭小小的零件,零件们在他手指间躲来躲去,很不听使唤。随后他去一家鞋厂管仓库,整日与牛皮们厮守在一起。不用说,一张牛皮就是一头牛。每天从他手里要出去许多头牛。这些牛加起来,可以撒遍他家乡村子里的山坡。
正干得欢实,厂子忽然停产了。一打听,原来厂里出口的皮鞋被俄罗斯海关扣下了,说是手续不齐。事情闹得挺大,变成了贸易纠纷,要摆明道理,得国家跟国家去说。登锁只好离开鞋厂,投奔新的去处。说是投奔,其实就是再找活儿干。现在的活儿不好找,找来找去,撞上了一家搬迁公司。搬迁公司的人说,你看你,长着一身硬肉,不用是埋没人才呢。登锁上下打量一眼自己,觉出身上的肉疙瘩一跳一跳的。
从此登锁成了搬迁公司的雇工。每天凌晨,他起个大早,随货车到一家住处,咣咣当当地把家什物器弄上车,再前往住宅新区,咣咣当当地把东西搬入新房子。新房子一般挺大,有好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收拾得特别光亮。有时登锁忍不住要打听房子的价格,一问便惊出一头汗。因为算起来,温州城里的这一套房子能抵得上老家一个村的所有房子。干活儿间隙,登锁不能随便转悠,就好奇地进卫生间,用一用里边的抽水马桶。那抽水马桶果然了得,不仅白亮得目光都打滑,旁边还装着一排按钮,电视机遥控似的。登锁站在那里,好半天才敢把尿撒出来。
干完上午的活儿,登锁继续待在公司里。如果还有事做,就再流些汗。如果没事做,就早些回家。所谓回家,便是回到出租房。出租房又小又暗,是与王七筒合租的。王七筒也在搬迁公司里干活儿,人长得精瘦,只是脖子有些歪,被人叫成了七筒。登锁和王七筒都是有家室的人。登锁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王七筒家皇也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再加一个女儿。有老婆孩子的人都想省钱,不能学着乞丐睡在街头,只好拼租一间小屋子。在小屋子里,因为相互间能说个话,日子便少些枯燥。天一擦黑,吃过简单的晚饭,他们就各自斜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话儿,说说老家的事儿,说说老婆孩子。说到老婆的时候,两个人的嘴巴会热烈些,说着说着,脸上便有了异样,跟着身上也有了异样。想想也怪,在家里整天与老婆待在一起,不觉得老婆有啥好,离开了一些日子,记忆里老婆的身子都是香的。
说过家里的粗细,他们也聊城里的事儿。只是城里的事比较多,有些有趣,有些让人迷糊。登锁就对卫生间的按钮很不明白。他对王七筒说,城里的人爱听小歌小曲,那玩意儿是不是播歌曲用的?王七筒咕咕咕笑起来,然后很有经验地指出,那是洗屁股用的。登锁吃了一惊,说屁股擦过就完了,还值得糟蹋水吗?王七筒说,城里人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身上每一处肉都要弄干净的。登锁说,那上面好几只按钮呢。王七筒说,有一只按钮管垫圈的,冬天坐下去冷,一揿钮儿,垫圈就热了。有一只按钮管着冲屁股的水,能让水柱猛一些或者柔一些。还有一只按钮专门管着冲屁股水的温度。登锁瞪大眼睛说,你怎么知道的?王七筒说,我先前也不明白,不明白就问,问了就明白了。登锁点点头说,你明白的事比我多。王七筒说,我不光问了,还寻思了。我寻思那东西主要是给女人用的。登锁心里晃了一下,说为什么呀?王七筒说,你想啊,男人坐马桶一天也就一回,女人可不能,一天里得坐很多回呢。
以后干活搬东西,登锁比较喜欢抽空去一下卫生间。如果遇上装按钮的抽水马桶,他会低头细看一番,心里冒起一些叹息的气泡。从卫生间出来,他的目光还会去捉拿女主人,捉拿住了,就不客气地瞄上一眼。差不多每一回,女主人的身样总是不错,屁股圆圆的很结实。登锁想,城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哩。 时间进入农历五月,公司的生意突然淡下来。按照当地习俗,五月多霉天,不宜于搬家迁居,否则是不吉利的。登锁想不到这些,脑子有点蒙。公司的人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每年都这样。你们要么回家探探亲,要么自己出去揽点散活儿,过了这一段再回来。公司的话说得豪爽,却不能安慰人。在公司做活儿是按工付钱的,没了活儿就没了工资。
王七筒犹豫了一天,回江西老家探亲去了。他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即他的儿子全身起了疱疹,得回去看看。登锁犹豫了一天,决定出去找些小工做。算起来,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儿子学费、房子补修、老婆关节风湿病要用的药,哪一样都逼得紧,哪一样都得靠他。他不能让自己歇下来。
第二天上午,登锁早早来到务工市场门口。那里聚着一大群打短工的人,一看模样便知道是瓦匠木匠和修理工。谁家的房子需要拆拆补补敲敲打打,就过来物色一个人或两个人带去。登锁没有手艺,心里有些虚。有人喊有没有做泥水的,好几个人呼地围上,登锁不敢凑过去。又有人喊木匠在哪里,一批人应声而出,登锁又不敢凑上去。太阳一点点爬高,变白了,寻工的人渐渐稀少。登锁站在那里,目光软软的,像一个没事瞎晃的人。
下一天登锁买了一把瓦刀,学着其他人拿在手里,胸中鼓一口气撑着。很快有个白胖男人走来,高声说我家要砌个东西。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我会我会。登锁也提起声音说,我会我会。白胖男人的眼光走一圈,落在登锁壮实的身上。他说,我要在平台上砌一间狗屋。登锁吓了一跳,嘴唇缩在一起。旁边的声音说,不就是弄个狗窝嘛,我拿手的。登锁赶紧把嘴巴张开,说我也拿手的。白胖男人不再说什么,朝登锁一勾头,示意跟着他走。
到了白胖男人家里,一条长毛小狗迎上来,活乱的蹦跳。白胖男人说,它叫跳跳,跳跳希望有一间好的房子。说着把登锁引到屋外一个挺大的平台上,在平台一角,已备有砖头水泥沙子。登锁蹲下身子拨弄着砖头,脑子一时想不出城里的狗房子应该是啥样子。好在白胖男人已有构想,他把手比划几下,说应该这样这样。登锁就拌了沙子水泥,按主人的说法,一块一块地砌砖头。
活儿干得生,时间就过得快。将近中午,才把屋子搭成形儿。白胖男人从房间里出来验收,一眼便看出小屋子有些斜。用手拍拍墙壁,似不稳实,使力一推,砖头们哗地扑地,塌成一堆。登锁呆在那儿,脸慢慢涨红。白胖男人说,这是豆腐渣工程嘛。想一想又说,害狗之心不可有,跳跳差点遇上人为之灾呀。再想一想,又说,我不能给你一分钱,还要愤怒地吼一声:岂有此理!
登锁离开白胖男人的家走到街上,脸上涂满了沮丧,同时肚子又饥又渴。太阳照下来,把他的影子矮在脚下。他往影子上狠狠跺一下脚,表示对自己的不满。然后他走进一家点心店,要了一碗面条,舔舔嘴唇,又要了一瓶啤酒。他把吃的喝的吞下去,肚子充实了些,心里却生出虚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身上的钱已经不多。前几天刚寄了一些钱给家里,下个月的房租费过几天又得续交。王七筒不在,他的一半得先垫上。登锁想,不行呀,我还得赶紧找事儿做。顿一顿,他又对自己说,面条好吃,啤酒也好喝,可你还没到放开吃喝的日子哩。
出了点心店,登锁沿着街道慢慢往前走。街道不宽,两边全是商店。他东张西望,很快看见一家商店门口贴着一张黄纸:招收18-25岁、身高1,60米以上女服务员2名。往前走一段路,又遇到一张招工告示:诚聘熟练厨师1名,月薪2000元。再往前走,居然又见着一张广告纸:急招电脑打字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登锁被这些与自己无关的招工启事牵引着,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当走完第三条街时,他累了。他看看天空,太阳开始西斜;看看附近,有一片花草拥挤的地方。他知道,城里人管这种地方叫街心公园。
他走进街心公园,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他的脑子木木的,要想点儿什么,又不知想点儿什么好。他的眼睛慢慢粘上,身子一歪,斜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半生不熟,夹着一些断断续续的梦。待他醒转,天已经黑了。眼前行人不多,偶尔走过来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的肚子仿佛跳入一只青蛙,开始响起咕咕的声音。他站起身往外走,走了几步,膝盖突然一痛,引得嘴巴直哈气--原来他撞上了一尊塑像。定睛一看,是一只铜人,有真人那么高。他生气地一推铜像,铜像晃一下,像是打了个趔趄。 登锁走到路边,买了一只麦饼,边啃边看街景。街上车子很多,都急性子地跑来跑去,其间有一辆人力板车慢慢地走。走近了,原来板车上装着回收的废品。登锁眼睛使劲眨一下,脑子里闪出一道光:刚才那塑像是铜的,似乎还站不稳实。
登锁转身踅回街心公园,凑到那铜像跟前。他再次使力推一下,铜像明显地摆动。蹲下身细看,原来塑像是用四颗螺帽拧在地上的,现在两颗螺帽竟然不见,另两颗也已松掉。登锁顺势坐在地上,用胳膊绕住塑像的腿,心想这铜人大概是空心的,但也得有二三百斤哩。他张开嘴巴吸足一口气,又呼出来,心里已打定主意。
登锁花了半个小时走回出租房。他先查看那辆笨重的破自行车,自行车是王七筒掏四十元买回来的,花钱不多,用处不少。登锁不会骑车,却时常搭车去赶公司的活儿。眼下自行车沉默地立在屋角,像一头牛,让人放心。登锁转身在装衣裳的纸箱里翻找,没找到什么,就把眼光斜向床铺。他抖抖褥子,抽出破旧的被单,卷成团儿夹在自行车后座。接着,他的手在杂乱的桌屉里摸掏,找到一把沾着锈斑的扳手。现在,一切都准备妥了。登锁躺在床上,安心等候时间的消失。
夜慢慢往深里走。登锁估摸差不多了,开门推出自行车,拐过两条小街,上了大街。此时街上行人稀少,显得挺寡淡。他推着车,不能走快,心里有点怨自己没学会骑车。
到了街心公园,他张望几下,没见着人影,就把自行车支住,掏出扳手矮下身子,将铜人脚下的两只螺帽拧开,然后抖开被单蒙住铜人。他吸一口气,拦腰抱住铜人,竟没有提起。铜人比预料的要沉一些。他扎住脚步,再运运气,铜人脱离了地面,横在他怀里。他小心着走几步,把铜人搁在车子后座上。车子一下子吃力起来。
吃力的自行车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旁边不时有出租车嗖嗖地跑过,但谁也不愿意去注意这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男人。不过登锁自己心里有些慌张,好几次让车头扭来扭去,差点使铜人滑下来。夜里没有太阳,可他的脑袋沾满了汗珠,一甩头,地上便多出一串水滴。半小时的路,走了一小时还不够。
终于到达出租房,登锁把铜人立在屋子中间,抢过桌上的茶杯,一气把杯中的水喝尽。然后他围着铜人走一圈,心里想,明天得找个人,使劲卖个好价钱。这样一想,心里生出舒坦。有了这种舒坦,他连脸也懒得洗,一头栽到床上,很快呼呼睡去。
上午醒来有些晚。登锁弹开眼睛,看见自己的被单直挺挺竖在那儿,显得有点怪。被单上还破开一个口子,露出深黄的颜色。登锁起来潦草洗了脸,站到铜人跟前,一把扯掉被单。
昨晚与铜人见面相处都在暗色里,没留意是个啥样子。现在看清楚了,是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那个,小脸尖尖的,奶子鼓鼓的;转到背后,那腰肢用劲杀进去,小得像一棵菜,屁股则好看地翘起。虽然穿着连衣裙,身子却起起伏伏的。登锁看得有点愣,心想这女人造得真像个样子。又想,昨晚用破被单捂她一夜,算是委屈她了。他捡起被单,扔到一边,又退后几步,上上下下打量女人一回。
时候显然不早了,登锁简单吃了点东西紧着出门。他知道往哪里走。在这一带,散着好几家废品回收点,有的近些,有的远些。登锁不要近的,他见到一家,走了过去,再见到一家,又走了过去。遇到第三家的时候,登锁才让自己走进去。
在一堆堆废品的包围中,坐着一胖一瘦两个男人。他们看见进来一个人,手里空着,就不准备放在眼里。瘦的男人淡淡地说,有什么卖的吗?登锁说,我有一大块铜。瘦的男人说,一大块是多大?登锁用手比划一下,说这么大。两个男人立即端正了脸。胖的男人说,我很少见过这么大的铜块。登锁说,我有,但要给个好价。胖的男人说,价钱亏不了你,可我还没见着铜的成色。登锁说,铜还有啥成色?胖的男人说,铜有时跟锡混在一起,有时跟铝混在一起,有时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纯度都不一样的。登锁发了愣,想一想说,那你们过去看看吧。
两个男人凑一下头,由胖的男人跟登锁走。登锁一边走一边要给铜人来路找个搪塞的说法。登锁说,这铜块是别人托我卖的。胖的男人说,嗯。登锁说,说是铜块其实是铜像。胖的男人说,嗯。登锁说,铜像的模样像个人呢。胖的男人说,嗯。嗯过之后,又笑一笑说,管它是个人还是只狗,扔到炼炉里就是一块铜疙瘩。登锁见他不在意,就不再说话。
两个人默着脸往前走。天气不错,尽管是小街,路上仍走动着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男人不用去留意,女人大多已穿着露胳膊露腿的衣裳。登锁觉得,路上遇见的女人没一个比铜像女人好看,比脸比不上,比腰肢也比不过。他想,那么好看的一个女人,不久就会被丢进火里,把脸烧焦了,把腰肢烧没了,然后变成七曲八扭的一团。登锁的脚步慢下来。胖的男人说,怎么啦?登锁说,我的铜像是个女人。胖的男人一挥手说,男人女人都是一个价。登锁说,能不能不把女人搁到炼炉里?胖的男人说,你傻呀,不把女人放入炼炉,怎么变成其他东西?登锁说,会变成什么东西?胖的男人说,那可说不准,工厂收购了去,爱做什么是什么。登锁止住脚步,难为情地说,铜像我不卖了。胖的男人说,为什么为什么?登锁说,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卖了。胖的男人说,我会给一个让你高兴的价钱。登锁摇摇头说,跟价钱没有关系。胖的男人愣怔着说,你……你这不是耍人吗?登锁让一步说,这样吧,这事容我再想想,想好了要卖,还是去找你。胖的男人本来要生气,一听这话便不能生气了。他看看登锁,一时说不出话,只好转过身悻悻走了。
登锁回到出租房,把自己扔在床上。他不明白自己刚才为啥变了主意,所以也不知道
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侧过头,细细打量铜像。这女人真的是美呀,那脸蛋、那胸部、那小腰,处处显着一股子味儿。登锁不敢把老婆拿出来,就把村子里所有俊俏的女人在脑子里过一遍,可谁也赶不上眼前这个女人。登锁又把搬运时遇到的女主人想出几个来,还是没法跟她比。登锁想,这样的女人大概只能在电影里找呢。
登锁爬起身,凑到铜像跟前。他的手禁不住伸出去,贴在女人的脸上,贴一会儿,又往下走,经过乳房来到腰肢。然后他绕两步,把自己的手引到女人的屁股上。虽然隔着裙子,但他能感触到手中的屁股翘翘的,一点儿不往下掉。登锁想,怪不得城里人家的抽水马桶要装洗屁股龙头,这样的屁股配得上的。这样想着,他的腹部有了感觉,好像一下子长出了力气。他慌慌地丢了手,重新躺回床上。
说起来,登锁很久没沾女人了。在家里,他是贪的。跑不过几天,就跟老婆打一回交道。有时老婆腿关节发痛,不乐意,登锁就忍,忍不住了,赖着脸儿要,老婆便给了。到了城里,情况不一样了。这儿的女人一个比一个鲜亮,但跟他没有一点点关系。小巷小店里倒有可以打交道的女人,可那是碰也不能碰的。他来城里是为了赚钱,得把心收着,不能有别的念想。有时日子长了,他的身子禁不住要动响。这时他便让自己使劲干活儿,身上的力气用尽了,那东西也就不能撒野了。
现在,登锁却很想让自己撒一回野。他把这个女人弄到自己屋子里,暂时就算是他的人了。守着这样的女人,他好歹要与她打一回交道的。说一句好听的话,他跟这个女人有缘哩。登锁一边想着一边就将手伸进裤子里。他浑身的肉一下子绷紧,鼻子里的气也热了。他侧头瞧着铜像,那脸蛋那奶子那细腰,样样逗着人。他闭上眼睛,同样的脸蛋奶子细腰,都变成了肉色,活了似的。登锁哼哼两声,身子腾空了,像离开了床。
回落到床上后,登锁脑子木了一会儿,想:不卖了不卖了。
第二天,登锁决定让女人待在家里,自己出去找事做。他想了想,还是不能学无头苍蝇,就又去了劳务市场门口,与一大群瓦匠木匠混在一起。不过此时他已不敢摆出气势,怕揽到不在行的活儿。心里一犹豫,手脚便赶不过人家。周围的人少了一些,又少了一些。剩下的人渐渐不安,都大了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登锁站在那儿,气愤地想,这城里热热闹闹的,各种事情像田里的秧苗一样多,可怎么就没有耗力气的活儿呢。
终于有人沮丧了,把身子蹲在地上。登锁丢口气儿,也蹲下身子。他瞥见旁边蹲着的人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又从裤兜里抽出一卷报纸,展开了看--原来是《都市早报》。这报纸登锁眼熟,以前掏钱买过几次,上面啥事儿都有,挺抓人的。现在,旁边的人撇开其他文字,直接去看招工信息。他看得很慢,吸一口烟,看几行字。登锁也想知道招的什么工,长了脖子凑过去。旁边的人盯他一眼,从一叠报纸中抽出两张给他,有点打发的意思。登锁把两张报纸前后粗翻一下,再细细地看。他看到一块出门旅游的文字,丢开了;又看到一堆阿拉伯人打仗的文字,也丢开了。突然,一行题目“街心天使被盗,警方介入调查”跳入眼中。登锁的眼睛猛眨两下,往小字里看,上边果然写着跟自己有关的事儿,说美丽天使的消失使街头减少了一道风景,说市民们很生气纷纷表示不满。登锁脑子一下子凝住,愣了几秒钟,跳起身就走。旁边的人不高兴地叫喊,我的报纸我的报纸。登锁扔下报纸,脚步移动得又快又乱。
回到住处,登锁关上门,一屁股坐在床上。他想,我惹祸了,我成盗贼了。停一停,他又想,警察要认识我,在设法找我呢。他抬起头,看一眼铜像,丧气地低下。他对自己说,到底是女人,招惹不得呀。
登锁站起身,不知干点儿什么好。他茫然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看见桌子上的茶缸。他端起茶缸,是空的,便在水龙头下取了水,咕咚咕咚喝下。凉水使他稍稍清醒。他想城市这么大,警察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并不是容易的。问题是女人老站在家里,又没法让她躲起来,迟早会被人撞见。唯一的办法是把铜像切开,变成一块块铜料。铜料不是女人,女人不见了,他的担心也不见了。
主意打定,登锁从杂物抽屉里找出一把榔头,对准铜像敲了敲。清脆的声音响起,但响得厚实。铜像虽是空心,却不是榔头能对付得了的。登锁想了想,重新出门,寻到五金商店买下一把钢锯。钢锯有点贵,让他吸了吸嘴,但想想铜料总归可以换钱,又顺了气。回到屋,他把铜像周身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从胳膊下手。这胳膊又圆又细,轻轻一握,能含在掌里。
登锁拿茶缸取来水,把锯片打湿,然后叉开双腿,把铜锯架在胳膊上,开始拉动。两种金属咬在一起,发出呜呜的声音。声音响了片刻,登锁凑近一看,仅裂开浅浅的缝隙。看来铜像顽强着呢。不过浅浅的缝隙还是给登锁添了气。他不怕用力气,他的胳膊比这细胳膊要壮粗好几倍,再说他已两天没好好干活了,身上的汗水憋得慌哩。
登锁脱掉衣裳,两条胳膊上的肉疙瘩亮了出来。他一用劲,肉疙瘩便变得硬邦邦的,好像皮肤下藏着拳头。这拳头随着锯片的来回拉动一突一突的。不多一会儿,汗水漫漫渗出,在身上涂了一层油。登锁歇了手,瞧瞧那缝隙,已深进去一大半。他想,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本领,现在该用上榔头了。他取过榔头,攥紧了使力挥去,咣的一声,铜胳膊歪了;又咣的一声,铜胳膊弯向身后。他伸手一拧,胳膊离开女人,到了自己手里。
登锁把铜胳膊掂了掂,又用手掌捋一遍,丢到床上。一条胳膊已费了不少时间,要把一整个铜像变成互不相干的散件,得搭上一大堆时间呢。登锁突然觉得口渴,肚子也提醒似的叫了起来。不知不觉,已到午饭的点儿了。
登锁不愿意自己做饭,就套上衣服,出去到附近的小店买了两个馒头。犹豫一下,又要了一瓶啤酒和一包花生。他边往回走边啃馒头,进到屋里,馒头已经吃完。他坐在床边,一口咬开瓶盖,嘴巴粘着瓶口久久不放。放开时,啤酒下去了一截。他舒口气,抓了几颗花生米扔入嘴里,然后抬眼看了看铜像。此时的铜像不一样了!登锁愣了愣,心里慌了一下。一个好看的女人,一个只在电影里才能找到的女人,突然就失掉一条胳膊了。
整个上午,登锁心急,眼里只有铜像。不知怎么,现在女人又回来了。铜像变成了女人!
眼下这个女人,仍然飘飘的,妙妙的,把全村女人的好眼好鼻拿出来,再加起来,也不一定比得上的。怪不得城里人管她叫天使。天使应当是该有的都有着,该好的都好着。可现在,女人的右边断了臂,自己的目光在那个地方老是扑空。不用说,这条胳膊对女人很重要。伸出去,能摘花采叶。抬起来,能修理脸面。有的时候,还要柔柔地放在男人胸膛上呢。这样想着,登锁忍不住又看了女人一眼。他看到女人脸上有些哀哀的东西。
登锁心里难受起来。他举起瓶子,把剩下的啤酒慢慢倒进喉咙。他想打个嗝,嘴巴张一下,发出来的却是一句骂:你他妈造孽呀!他站起来,走到女人背后,一把搂住她的身子。他的心里忽然有点酸酸的,又有点暖暖的。
过一会儿,登锁松开女人,拿回床上的那条胳膊,往她右边比划。他想接回胳膊。他琢磨许久,没别的办法,只能用布条包扎。他弯了身开始翻找,很快找到一条红色破背心,噗地撕下一条,然后架好胳膊,使力绑住断裂处。
现在,女人又长出了胳膊,只是有些垂,看上去受了伤的样子,红的布条则像染了血。登锁坐回床沿,不说话。瞧一眼女人,女人也不说话。登锁觉得,女人心里是又高兴又不高兴的。高兴,是明白他心疼她,让她身子变周全了。不高兴,是因为他到底弄伤了她,她身上有了痛处。登锁想,我不该再亏欠她了,我得把她送回去。这个念头一起,他以为自己会吃一惊,但他没有。既然不再伤她,总不能让她老在家里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