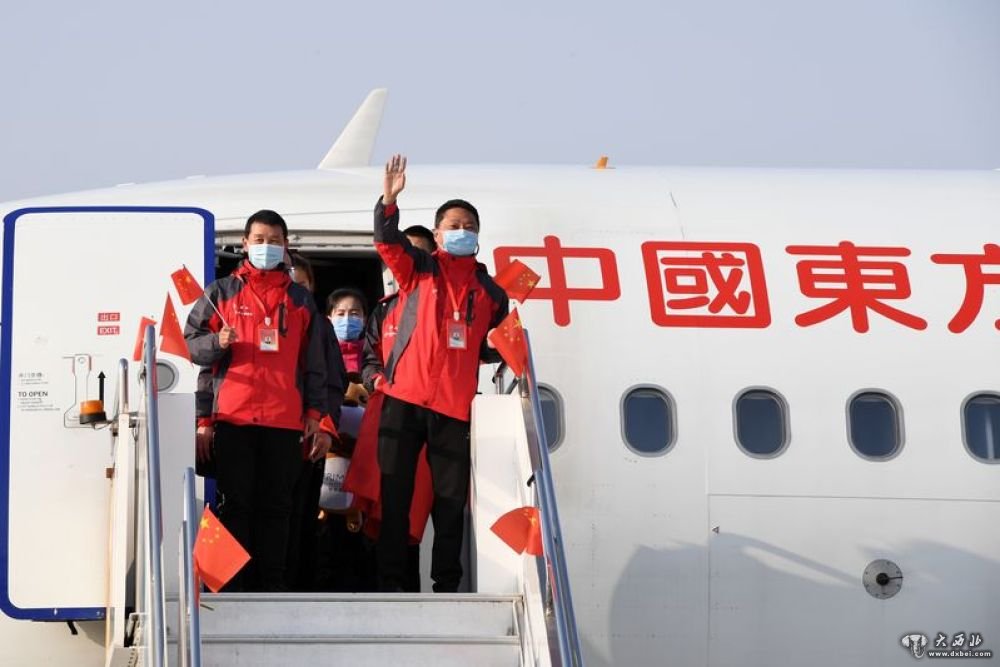山丹明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并且容易观赏到的一段,是从绣花庙到新河的长城口一带——这里地势较高,降雨量少,又因远离村落而较少受到人们生产活动带来的破坏。对于路过此地漫游丝绸之路的游客而言,在整个河西走廊,山丹新河的长城口是惟一距公路最近,城墙又较完整的地点。新河一带的明长城墙高在5米左右,顶宽2米左右,顶部外侧(北边)加筑有矮墙,现存残高约50厘米,称为“女儿墙”。
在山丹新河一带,有些农民家中还保留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石夯锤。据一位经常为人家夯打土墙的农民告诉我,他用的一柄石夯锤是从他爷爷手中传下来的。他还相当肯定地认为山丹的明长城就是用他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这种石夯锤和板椽夯筑而成的。我想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明长城城墙里,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夹埋在其中的草绳,甚至木椽(在高大的烽燧和敌台的四角更是容易见到木椽)。既然使用“夯土板筑”的技术,就只有用人手一柄的石夯锤——用较分散和较小的着力点,才能把土夯实。如果用众人拽抬的大夯来夯打,则会因集中而又很大的冲击力造成“版筑”变形甚至墙体垮塌。
有人说:夯筑长城的土被蒸过,所以不长草……还有人说:夯打长城时,每打完一层都要彻底晒干,再打下一层……
就这些土拉巴唧的山丹明长城,细细地去看、去听,名堂多着呢!
绣花庙的牧羊人
“武威盆地”和“酒(泉)张(掖)盆地”之间是一片隆起的山地,这片山地是走廊南边从祁连山伸出的焉支山,与走廊北边的龙首山两山之间的结合部及一系列坡积——冲积带所构成。绣花庙就在这片山地的最高处。
绣花庙现在的确没有庙,而且就连庙的痕迹也不知在哪里,耸立在山坡上的只是长城和营盘的残垣断壁。地方志中也没有关于绣花庙的来历、供奉神明的记载,惟一的注解就是绣花庙从前叫“定羌庙”这一点。带着迷惑不解和对绣花庙一带长城、营盘的兴趣,我去了绣花庙。
在绣花庙营盘遗址西边、长城脚下,住着一户人家。一间砖瓦房面朝南——也朝着公路,房后是羊圈,整个房屋及羊圈的东边是一道比屋顶还要高的土坎,土坎上拴着一条狗,有生人到来那狗立即狂叫了起来……
屋子里住着山丹县老军乡李泉村的农民邢天华一家人。绣花庙一带地势较高,海拔在2000米以上,平坦而广阔的山地因无水灌溉没法种庄稼,就成了一片牧场——如今这片牧场属老军乡政府直接管辖。邢天华及另两家也散住在绣花庙山坡上的牧羊人都是乡牧场的放牧承包人。据牧场一位负责人讲,乡牧场共有1000只羊。
农民出身的邢天华36岁,对于“放羊好还是种地好”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回答:“现在地越来越难种……成本高——施了化肥,天不下雨,就连化肥钱都收不回来。我家有十几亩地,全是旱地。今年天旱,亩产量还不到一百斤,自己一家的口粮都不够……我放羊、种地两头兼顾,放羊一年还能收入八九千元。”邢天华的妻子说:“我们这里天爷好(雨水好),就收成也好、羊也好……”邢天华接着说:“像今年这种天气,冬天羊羔的产量就少,明年的收入就要受影响。”
绣花庙、汉、明长城边的牧人除新河富昌堡遗址下之外,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羊圈——绣花庙度过的。白天邢天华去放羊,羊圈的家里还需有人看门、做饭,所以他的妻子和母亲轮流住在牧场。秋冬季节,家里的农活较闲,母亲和妻子、假期里还有小学刚毕业的女儿,一家人都在牧场。
邢天华的笃信天主教的岳母也随了承包牧场放羊的儿子住在绣花庙。她告诉我:自己的儿女中一个是神甫、一个是修女。邢天华及母亲、妻子也都信奉天主教,我曾指着邢天华的女儿问邢母:“她信不信?”邢母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当然信!咋能不信呢?”邢天华的妻子说下学期不打算叫女儿上学了,“家中太忙了。”我问道:“她自己愿意吗?”“开学了再看,她实在要上就上初中去。”高中毕业的邢天华似乎对女儿上不上学的事不大关心--对此未发表意见。
既然放羊还可增加一些收入,像邢天华家中的地也还照样种。那么,是不是人人都视放羊为“美差”呢?邢天华的妻子说,现在村上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放羊,还说:“就是羊拉金子也不去受那个罪……”邢天华还有一个已初中毕业、16岁的儿子,“也不愿放羊,说是要出去打工。”邢母说道。
绣花庙一带由于干旱少雨,羊群的放牧必须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放羊出圈,以使羊吃到带露水的草。另外,邢天华每天早上还要赶羊穿过312国道,去南边的焉支山脚下找积了水的水洼,或者走更远到有水井的地方给羊饮水。然后,再将羊群赶回到北山——属龙首山脉的一座叫“长沟山”的山坡上。于是,邢天华和羊群每天还得两次从绣花庙的汉、明长城遗址上穿过……
村里农家宅院前
然而,邢天华对这些长城还有“绣花庙”的来历几乎一无所知。
今年60多岁的邢天华的岳父讲:从前,这里叫“定羌庙”,我小时候就没见过庙,只见到有齐腰高的庙的残墙,砖的……
再问邢天华的岳父是否知道这些“边墙”(见诸于史料的明长城的名称,山丹的农民皆如此称谓)是何时修筑的?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听别人说过?”“都说是秦始皇修的……”
绣花庙一带的长城及营盘颇具规模——在长沟山与焉支山之间的马鞍形山地上,汉、明代长城以东南—西北的走向蜿蜒匍匐在大地上。已呈埂形的汉长城及其沟壕(汉塞)在明长城的北边,两列长城相距仅十余米,明长城的营盘依傍、坐落在明长城的南侧,残存的营盘城廓四周约有百米见方。奇怪的是它的东西各相距数十米的两个盆形地貌,问邢天华及其岳父,都说是“涝池”。
昔日的绣花庙只剩下这残砖瓦砾,干旱缺水地区村庄用来集河、渠水,以供人畜饮用的水池,在河西走廊现已基本不用或只供牲畜饮用——赖电力深井之功)。然而,从它所处的地势、位置及那一带水源条件分析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这两个约百米见方的“涝池”的体积,比一个村庄的可供数百人及牲畜饮用的涝池不知大了多少倍!据道光十五年(1835)修《山丹县志》记载:定羌庙为“塘”——“驿塘之设,即置邮而传命也。”编制为“原额马一十六匹,夫六名。”又如何用得着如此之大的两个“涝池”呢?
峡口城堡里的村庄
长城从绣花庙北边的长沟山下往西延伸数公里,向北折转爬上山坡,那山坡的脚下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峡谷,这个在地方志及现在的当地人仍称为“峡口”的峡谷,历史上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道天险。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曾有“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的诗句。
我在绣花庙听邢天华的岳父讲,现住峡口城堡里的戴学俭小时候曾在绣花庙居住过,并且他的爷爷曾在定羌庙营盘里任职,也许戴学俭知道一些有关绣花庙的故事?
现在的峡口成了一个村庄,正式的地名就叫“峡口村”。现有居民一百一十户,六百多口。村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峡口城堡里,城堡的西边厚实而高大的城墙上,有一个拱形门洞,那条旧日的丝绸之路大道就从门洞下穿过。
整个门洞还保留了砖券——据峡口的村民讲,从前整个峡口城堡的黄土夯筑墙体外面都是砖包的,后来村民们修自家的屋院时,陆续从城墙上拆那砖,竟然将诺大一座城墙的砖给拆光了!初听人们讲这话时,心里多少有点不大相信,后来在村里见到家家户户的院墙、屋基、台阶甚至猪圈都是用巨大的砖块砌的,方才相信。
据66岁的戴学俭讲:今天峡口村的居民都是从前在这里做生意的人逐渐定居下来的。他还说:“从前,山丹城里的姓氏没有峡口的多!”戴学俭在家里翻出一块他爷爷的“牌位”——文革期间,他冒险将“牌位”装于瓷坛内埋藏起来,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牌位”上记载着他的爷爷于民国二十五年去世。据说,戴学俭的爷爷生前在定羌庙是有一定权势的,人称“四老”(排行为四),经营的车马店就叫“戴家店”。峡口村民唐学贤说:“戴家在峡口是有名的财东,在定羌庙可能也有生意……”
我问从小在定羌庙长大的戴学俭,为什么后来要搬家到峡口城堡里居住?他说:“贼多得很,住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