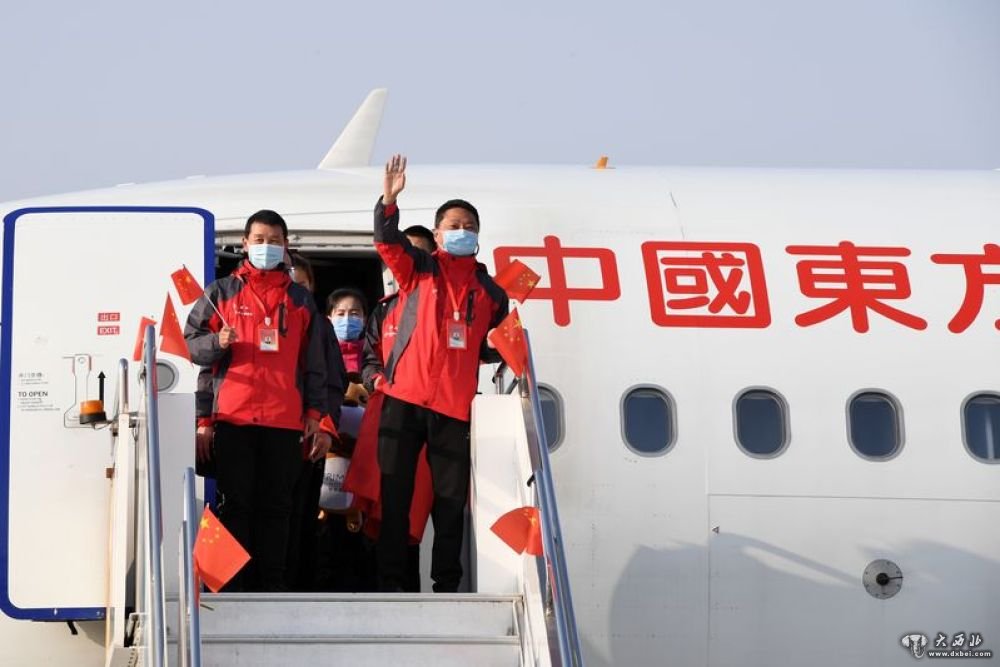倾谈,是古已有之的一种交流思想感情的形式。三二友好,促膝谈心,就是倾谈。但是倾谈常常被人与清谈混淆并论,带有贬意。
说到清谈,有它的历史。
自从魏晋崇尚清谈之风之后,名士之流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祖述老子庄周的无为思想,排弃世务,专谈玄理,形成一股颓风。到了晋末王衍之徒,更助长了这种清谈的习气,终于导致晋祚之亡,因此被后世之人评为“清谈误国”。
对于“玩世不恭,清谈误国”的清谈,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曾经流露过反对的情绪。《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有一次和谢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目不暇给。今四邻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所致焉?”
王羲之没有反驳谢安的话,但已可看出王羲之是厌恶清谈的。
考察魏晋清谈,几经变化,魏之名士,好评骘人物;晋之名流,好高谈玄理。评人物,有可取之处,如刘邵在“人物志”中就曾评述道:“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似乎谈论之间,有举荐人才,以治天下的意思。我们看《三国演义》,有人观察曹操之后,对他下了评语:“子承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可是曹操却大喜,因为乱世英雄可以创大业。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却引起刘备的惊恐,因为英雄可以创大业,岂不招致曹操的忌恨?于是刘备演了一场闻雷声而失箸的小喜剧。
谈玄理则不同,纯粹出于消极遁世,侈言清静无为,所以王羲之不以为然。
清谈之成为贬辞,可说起因于晋名士的颓废。到了后世,就被人引以为忌了。其实,抛去清谈之词,改为漫谈、倾谈,就不见得不能谈了,问题在于谈的是什么?
最近读到一本书,书名《鹪鹩庵笔尘》,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知己朋友敦诚写的,刻印于清嘉庆年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另有一本书《四松堂集》就是他的诗集四卷。《敬亭小传》说他“以病告退,素耽山水”,“好宾客,日引文士,分韵擘笺,不以晨夕间”。因之他好倾谈,在《笔尘》中对倾谈发了一番议论,他说: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缽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论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
这番议论,可说对倾谈的情操有所发挥,我也觉得很有见解。敦诚的谈旨,在于真正地交流思想感情,包括对知识、学术、社会、人生等的体会,似此倾谈,的确可称为上乘。
这种上乘谈的情操,在现代,曾见之于鲁迅。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曾经常到“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饮茶漫谈,他们把这种漫谈作为启发智慧引写文章的资料。后来内山完造还凭漫谈写成专书,鲁迅为他的书写过序文。由此可见,倾谈是必要的,是有高尚情操的。不论对茶对酒,都可款友倾谈,只要有上乘的情操就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最难风雨故人来”,“寒夜客来茶当酒”……诗情友趣,实在是可以倾谈个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