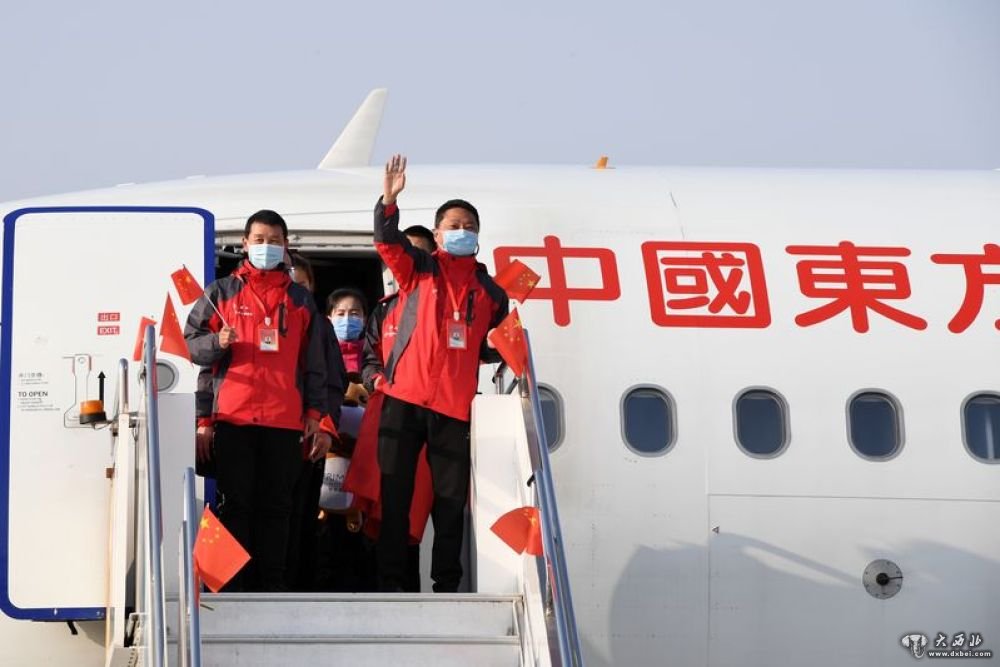译笔藏万军
德国作家格林所以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逃避之路》,是因为“不论我到各地旅行还是执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逃避”.对于格林在中国的知音傅惟慈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踩一段钢索,战战兢兢,唯恐栽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活儿(正业之外),打扫不完的卫生,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他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他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他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之后,我常常自己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偶然间,我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从“反右”到“文革”,傅惟慈曾无尽无休地受到批判,原因在翻译了几部德国文学作品。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在“大跃进”前后和“反右倾”运动间隙中偷时间译出的。后来的翻译家杨武能说,这部书翻译水平之高,使得“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亨利希·曼的《臣仆》,傅惟慈着手翻译不久就赶上“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完成时“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快临头,稿子一直在出版社搁置了十余年才见天日。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月中,要认真译一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只能在风浪的间歇中偷一点时间,另一方面又惧怕舆论的压力,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他把要译的书籍拆散,夹在经典着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窥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
“文革”前后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他与董乐山等老一辈翻译家,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他说:“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
“文革”来了,一切事情都出了轨,他的小小的翻译事业自然也翻了车。一搁笔就是十年。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历劫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一本天主教徒作家质疑教义的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天才画家的故事《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文革’中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不再玩这一文字游戏了。”
牌戏人生的乐趣
印象中,每次见傅先生,他都声音洪亮,谈兴很浓。来客总会不由自主跟着他的话语神游。沉默的间隙,猛然发现,他高大的身架陷在椅子里,有些别扭。两条长腿、一双大脚委屈地缩在那里,衬得桌椅那样小。只在告别的时候,他才费力站起来,送你几步。这双曾经满世界溜达的大脚,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
常去做客的朋友说,这些年几乎是眼见声如洪钟高高大大的傅先生,一点点衰老下去的。生死并不是他畏惧的。女儿说他是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惧怕形神的消散。2007年的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医疗研究机构接收公民捐赠遗体的消息,立即与老伴一起跑完各种复杂手续,签下了遗体捐赠书。他对女儿们说,醒不来的那一天,直接找车拉走了事,不用举行任何仪式。
聚会中,那些“老愤青”们同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小“粉丝”们一脸崇拜围坐他身边。人们只感受到他智慧的光环,很少留心,他在什么时候坐在角落里沉默,或者回到了屋里。那是他疲惫的时候。
晚年的傅先生其实一直在与时间和衰老抗争。那是他一个人的战争。
他是中国最老的背包客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旅行概念的时候,他已经利用教书之便,漫游欧洲了。甚至在82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大街上骑自行车穿行。在中国,他喜欢一个人,背着小包,寻找人烟稀少的所在。或是僻远的乡野,或是一个边贸小镇,常常随遇而安,只根据兴致所至。那时候他扛着一个胶片机,浪费了许多胶片,也拍了一些行家颇为赞赏的照片。他把那些异域的天空,偏远的街巷,古老的画面都冲洗出来,挂在屋里抬眼就可以望见的地方。
2009年摔坏了胯骨,八十多岁的人了,动手术见效快,却很危险,医院建议回家吃药静养。女儿们明白,这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日子将要在床上度过,这对于一生追求自由的老父亲来说,无异于一种囚禁。冒着风险,女儿们签字,把父亲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很成功,87岁的傅惟慈又站起来了。天好的时候,兴致来了,他会骑着电动三轮车上街,逛胡同,逛后海,甚至一个人跑到前门。我猜想,他倔强的白头发肯定在风里自由地欢呼。但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些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起七八十年前,在后海的祖宅里,被父亲关在书房里读“子曰诗云”的童年?或者想起穿越大半个中国寻求自由的青年时代?想起曾经走过的那些偏僻荒野和异国文明?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沉醉在自在出行的快活里?无论如何,他的双脚仍然没有束缚,他的世界没有变小,真好。
他一直保持老派文人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的报,他要第一个拿来看。看到有趣的新闻,还要讲给女儿听,喜欢的文章,甚至兴致勃勃地念给她们,好像女儿还是当年那个读书的孩子。许多没有客人来访的日子,他总忍不住唠叨自己年轻时那些“老皇历”.
他对一切新鲜事物好奇。iPad迷你上市,他买来玩,听说有好书,他找来看。遇到喜欢的,从不吝惜夸赞。前两年喜欢上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自掏腰包买了一二十本,逢人就推荐。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好声音》看上了瘾,买来光盘,一期一期地看。有时朋友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叫上朋友一起看。这个爱好古典音乐的资深老乐迷,对流行音乐并无偏见,如同他的翻译既有严肃文学,也偶尔涉猎通俗小说一样。也许他从中看到了百味人生,也许这是他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是他唤起正在被时间侵蚀的生命热情的努力。无论如何,女儿们说,这个热闹的节目,傅先生看得很快乐。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