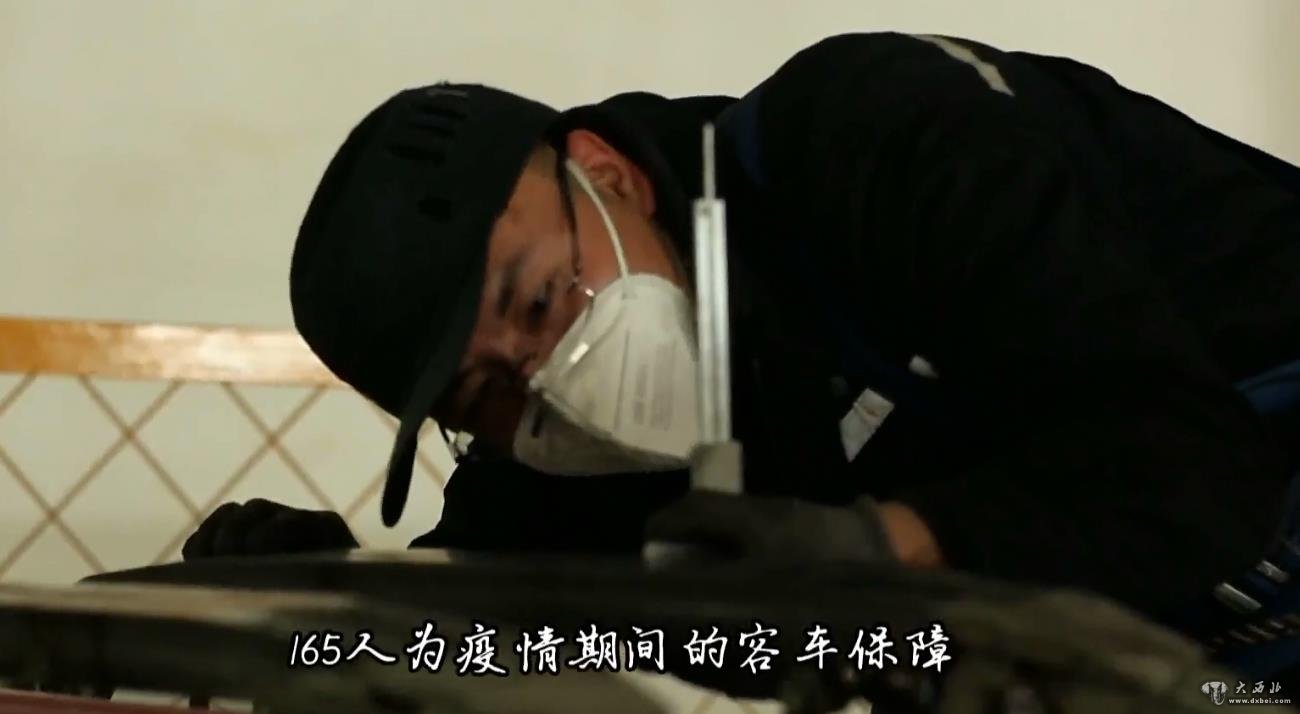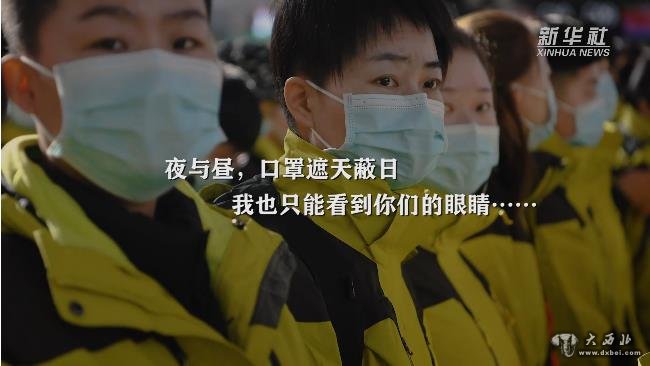殷代 122-147 7-8 6 16-26 22-44 215-240 1300-1100
李约瑟早就从一种艺术的马姿(现实中不可能)注意到了东西方之间马与马车之联系 。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印欧语词汇,Lubotsky认为汉语中的车和一些车具名词是吐火罗语借词 ,从而佐证了马车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车的读音在欧亚大陆亦很近似,安东尼等坚信马、四轮车(wagon)和马车与印欧语的传播密切相关 。殷墟遗址出土的马和马车无疑源于西方或北方。夏含夷注意到甲骨文中“车”出现于武丁后期,仅十六见,其中至少五次是人名或地名,另外四次似乎来自一次占卜,却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写法。他推测这种不稳定的写法表示当时是新近接触马车,正如现代语言中的外语借词的标准化之前有一个即兴变化阶段 。很少有证据表明商人在战斗中应用过马车;相反,有众多证据表明他们从西部或北部的敌人手中夺取马车。此外,车的零件如轴、轮、轩、辕、轭、辐、辖等均有车旁,亦表明汉字的创造者先认识整车,后认识车的零件。李家崖文化遗址中马骨和车马器的出土表明鬼方或土方、吉方等西、北方国使用马车不晚于殷商。《小孟鼎》、《师同鼎》、《多友鼎》记录了西周时代戎人使用马车的状况。欧亚草原上众多的车、马岩画亦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欧亚之间有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骑术与马、车大体同时出现在东亚。石璋如研究了 小屯及西北冈两处出土的遗物后指出车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骑马的战士也用弓。但弓与车的关系较密切,弓与步兵的关系次之,弓与马的关系又次之。仅M164墓中弓与马同坑出土,但骑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Goodrich仔细考察了古代中国骑乘与马鞍问题,指出战国时代才有大规模的骑兵队伍,秦汉时代才有使用马鞍的确证,二者均晚于中亚的斯基泰,应该充分考虑草原游牧民对中国骑马文化的影响 。叶慈在《马: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因素》 中指出,汉代以前中国和其北部邻居拥有的是一种矮小的本地土种马,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大宛等地引进良种马。西域良马和苜蓿的引进又一次促进了东亚养马业的发展。马因人工选育而改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亚养马早于或优于东亚。 “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马镫加强于人马的结合或共生关系,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而马镫很有可能是东方的发明 ,在蒙古西征和南征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马镫是东亚人对骑马术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 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细粒体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马是一种很难驯化却容易野化的动物。因此有野马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可能参与马的驯化活动。主要分布于东亚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2n=64,而普氏野马为2n=66,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物种。家马是由主要分布于中亚草原的塔尔潘(tarpan)野马(Equus Caballus Ferus)驯化而来。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tamed)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后来东亚居民学会和参与驯马的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驯马岩画可为佐证。家马的传播过程亦是驯马技术或风俗的普及过程。驯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领。
六、讨论与结语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 。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 。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
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 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 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 。在汉语 和阿尔泰语 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 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 。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 三星堆青铜群像 、西周蚌雕人头像 、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 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 和狩猎图像 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
林梅村曾肯定地指出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 。但根据他自己的考证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和楼兰地区的小河—古墓沟文化为吐火罗文化,其主人与牛、马、羊为伴,熟练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以定居畜牧或准游牧为生,都与丝绸没有任何瓜葛。因此吐火罗人开拓的是青铜之路,尽管他们后来在丝绸之路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难。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东亚的青铜器早于西亚。尽管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亦有人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看成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比西亚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铜时代之前上千年的红铜时代。举世公认中国不存在红铜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没有这一条目;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典型的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第二,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什么不同。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东亚、西亚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垒。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犹如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阿富汗)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
(责任编辑:陈冬梅)